

改革的努力应该放在制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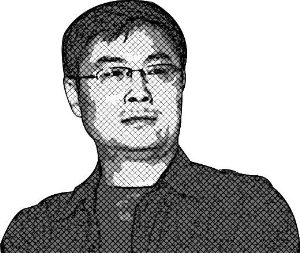
公共事务
文/邵建
改革国民性还是改革制度,上个世纪未曾解决的问题,今天依然横陈在我们面前。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有报道:东莞一女子被偷包,一巴西男子发现后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团伙群殴。当时有数十路人围观,但却无人相助。这是一个典型的看客现象,不用说,网络上充斥着国民素质低下的指责,进而有人还作这样的引申:如此国民和如此国民性,谈什么民主宪政。其实,这样的看法并非始自今天,近百年前的鲁迅,就是这种观点的早期代表。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写给他的学生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鲁迅的表述中,专制与共和,俱属制度话语,但比制度更要紧的却是国民性。如果国民性不变,即使专制变为共和,如鲁迅时代满清变成了民国,最终也不过一切照旧。关于国民性与政治、政府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中有过表述:“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吗?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鲁迅的意思很明显,没有好的国民,当然不会有好的政治、好的政府、好的制度。鉴于这样的认知,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以改变他们的精神来改变国民性,这种改变即鲁迅的“立人”。
鲁迅的观点带出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它不妨以这样一个问题形式出现:国民性和国体性,换言之,即素质与制度,两者谁决定谁、谁更重要。鲁迅的看法是,国民素质低下就不配享有优良的政治制度。因为有什么样的国民才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性质是由国民的性质决定的。国民性如此,制度何求。因而改革国民性而不是制度,便成为一种价值优先。
然而,和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却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有过一篇文章,叫《〈政治概论〉序》。这是胡适为一位北大教授朋友的著作写的序言,他和作者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问题由胡适朋友而起,该朋友认为:“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这其实正是胡适一贯的看法,但该朋友并不同意,他很直接地指出“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可以看到,这虽然是胡适朋友提出的问题,但其思路和鲁迅却如出一辙。
在制度与国民性的关系上,胡适虽然不是制度一元论者,但显然认为改造制度比改造国民性更重要。至少,胡适认为“历史上无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制度的改良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骤。我们不能使得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作恶”。转对民众而言,“民治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得多。”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本身就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他以英伦为例,在民治推进以前,也曾演出过很不像样的政治罪恶,可是经过1832年选举改革之后,英国公民的政治素质慢慢地被训练出来,从而成为一种政治先进。美国也是如此。胡适例举自己1912年和1916年在美国所经历过的两次大选,以他所接触的美国下层选民为例,指出:“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
改革国民性还是改革制度,上个世纪未曾解决的问题,今天依然横陈在我们面前。胡鲁的看法各有差异,各有道理;但比较之下,胡适的表述从不排他,正如他未必排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但更注重政治改造意义上的制度批判;因而他的看法也更值得我们今天注意。如果可以用我本人以前的表述作结,那么我对胡适的沿袭应该是这样:人是环境的动物,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首先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就会形成不同的国民性,这一点可以看看韩国和朝鲜,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嘛,何以反差如此巨大。所以,在改革国民性还是改革制度的两种选择中,我们今天的努力,无疑应该更多地放在制度改革上。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环渤海财经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