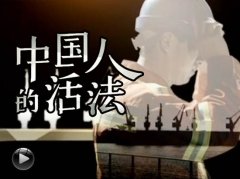企业并购的类型及操作要点(6)
摩尔根多么羡慕挨骂的达尔文
人类常常错误地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甚至长久地歪曲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本是从灵长目动物中分化发展而来的,可是我们早就忘记了这个事实,当一个名叫达尔文的科学家重新指出这个事实时,遭到了西方社会精英群体的一致攻击。这个故事显示了人类陷入认识的迷雾有多深。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出现在人类对于自身制度史的认识上。在现代人的描述中,民主制度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文明时代”的伟大创造,是直到近代才逐渐繁荣起来的一种游戏规则。远古时代则难免由残暴的国王大权独揽,独霸天下,他们一个个喜怒无常,专横跋扈,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所有的生命都在野蛮、专制的茫茫黑夜备受煎熬。
这种错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用美国学者霍贝尔的话说:“古老的政治哲学认为,初民生活在一个犬牙魔爪暴虐统治之下的社会里,这一认识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初民的法律》3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自古以来的这种错误猜测充分体现了“文明人”的自负,我们把制度结构中理性的部分理解为“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将制度结构中对人类构成伤害的部分看作是历史的馈赠。这种成见即使不能说是颠倒黑白,至少也必须指出,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最荒谬的误解。
跟达尔文大致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弗雷泽(《金枝》)和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用严谨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远古时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生活面貌,描述了原始文化和原始民主制度的真相,这标志着人类对于远古时代历史荒谬认识的终结。
摩尔根说:“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古代社会》1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原始社会,那些被称作酋长或者国王的政治领袖,其遴选、上任、下台都在民众的掌握之中。在有的酋邦,民众如果对国王不满意,只要送上几颗鹦鹉蛋就能让事情圆满解决。弗雷泽介绍说,在18世纪的某一天,非洲埃俄王国的一个民众代表团,受广大民众的托付,来到国王的宫殿,送给国王一些鹦鹉蛋作为礼物。这些礼物的含义是:国王您肩负执政的重任一定很累了,现在是应该考虑摆脱繁重忧劳、轻松地休息睡眠的时候了。国王收到这份礼物,知道民众已经不满意他了。他恭敬地向代表团致辞,感谢臣民为他的健康舒适着想,然后退回自己的内室去歇息。表面上看好像是去睡觉,实际上他一进房就必须吩咐他的女人将自己勒死。整个过程很快就会完成。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地上台执政。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期(《金枝》404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原始社会民主制度的完备和彻底由这故事可见一斑。
令人遗憾的是,弗雷泽和摩尔根的研究没有像达尔文的学说那样遭到全社会的反对和声讨,因而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至今为止,他们的学说局限于研究历史和人类学的少数学人之中,而不被公众所了解。也就是说,在公众的认识世界,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荒谬理解依然如故。
当年的达尔文一定没有意识到,那些对着他大吐唾沫的欧洲绅士们,为他进化论的普及所做的贡献是如何地与日月同辉。就此而言,一百个赫胥黎也比不过那些反对者们。
弗雷泽和摩尔根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发现没有遭到这么广泛的反对因而也就没有引起同样广泛的关注。一百多年后依然知者了了。当代人依然错误地认为,初民生活在一个犬牙魔爪暴虐统治之下的社会里。
假如弗雷泽和摩尔根地下有知,他们对当年几乎被“文明世界”的唾沫淹死的达尔文,该是多么羡慕不已。
好在人类在近几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一直在将原始先民(被称为野蛮人)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实践,转化为所谓“文明人”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资源。
中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3种刑法,并将其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洋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
子产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同时,子产承认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环渤海财经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